|
漫画下载器 在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20年前的马德胜是意气风发的警长,20年后他是鳏寡孤独的桦林舞王。 和另外两个主角王响(范伟饰)、龚彪(秦昊饰)不同,导演并没有给马德胜除了案件之外的情节和线索,观众只是在20年后三人的酒局上,得知其“不久前,老婆因为癌症走了”的碎片信息。 正是这样的变化,勾起了观众的好奇,到底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让马德胜变成了20年后的样子,周遭的一切好像都变了,马德胜也变了,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变。 随着《漫长的季节》口碑不断上升,剧中的演员和他们的表演被观众认为支撑起来了这个贯穿了20年的东北故事。相比起范伟和秦昊,饰演马德胜的陈明昊却鲜少被提起。 5月初的一个周末,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城东一栋被改造成排练厅的集装箱里见到了陈明昊,他正在为下个月的阿那亚戏剧节做准备。 在陈明昊看来,记者闯入了他的创作思路,打断了他正在享受的傍晚,让自己处于一个强烈的不安感中,这让他感觉到“危险”。 “但是,我喜欢这种危险和不确定的东西。”陈明昊说。 陈明昊饰马德胜图/受访者提供 以下是陈明昊的口述 从外到内,认识马德胜 早在《隐秘的角落》时,辛爽的团队就曾找过我,但是那个时候我去法国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了,时间没对上点,就没合作成。这次他们又找我,我就答应了。 有的演员挑本子,我更看重是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合作,所以我接下马德胜这个角色的时候,剧本甚至还没有打磨好,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马德胜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希望我能演出一个不同的警察来。 “大人演不过孩子,孩子演不过狗。”这是我们戏剧人的一个共识。舞台就那么大,没有演员可以控制观众看谁,舞台上的演员是靠重心吸引观众,所以浑身上下都是戏。 但舞台上积累的表演经验,在影视剧中,并不见得有用。因为影视剧最终呈现的是导演的调度,镜头的剪接,在一个景中,导演想让观众看到谁,观众自然可以看到谁。 马德胜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心里没谱,直到开机我也没谱。前后跨度时间有20年,20年里可能发生太多的事情了。 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大部分时间是从内而外塑造人物形象,通过自己对于人物的理解、体会和感受,来尽可能地往想要塑造的人物上去靠,但马德胜这个角色,我始终没找到感觉。 范伟和秦昊都是东北人,导演辛爽也是,但我不是,为了让我更好地感受东北的氛围,导演组从我进组就开始要求所有人在对戏走调度的过程中使用东北话,尽可能地把我带进这个氛围里来。 你也知道,东北话的感染力是非常大的。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有3个东北同学,半个学期我就被他们带走了。我还记得后来去演戏,一位导演把我说笑了,“看得出,你在尽力克制你的东北口音。” 由于东北气候的原因,不满足拍摄的条件,剧组把拍摄地点放在了昆明,宿舍、厂房包括路边的商店,王响家里的铸铁暖气、王阳卧室的红色毛毯、沈墨大爷家里的老虎沙发套,都带有年代感和东北特色。 但仅有口音和环境氛围,仍然无法让我感受到马德胜,直到开始化妆。 拍摄进度和场景的要求,我们的老年戏和中年戏并不是分开拍摄的,而是同期进行,相比起范伟和秦昊的妆,我化妆的时间最长,大约需要五个小时。有的时候早上起来要拍戏,半夜两三点钟就要开始化妆,贴脸、粘头套,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次性的,每天拍完就要揭掉,第二天重新弄。我甚至尝试过亲自制作假发,那都是需要一根一根用镊子安装在发套上,工序十分复杂。 有时化着化着我就睡着了,睁开眼迷迷糊糊一看,我已经成老头了。老年这东西特强烈,感觉是马德胜年轻时的困境、内心的挣扎一下子就都推到这儿了。 老年马德胜图/受访者提供 我是在化妆镜前找到马德胜的感觉的。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陌生人时,这张面皮激发了我去填充情感的冲动,就好像在身体里做了一个实验。看着自己一步步变老,让我和马德胜这个角色突然有了情感,自己突然老了以后,我去思考年轻的马德胜是怎样的,是怎么成为这样拧巴的性格和状态,就一下子容易了很多。 但真正表演的时候,每一条拍摄的情感仍然是不一样的。回过头来去想,还是有遗憾的地方。 比如辞职前马德胜和朱局的那段戏,案子没破,我憋了一肚子气去干仗,发泄,然后脱衣服扬长而去。现在我回想起来,应该还有别的更好的处理方式。是不是更克制,憋着点情绪,效果会更好,现在我不知道了。 创作就是这样,当时的情绪上来了就选择了当时认为最对的事情,回过头来再想的时候,往往就会不一样。有的观众就可能会接受当时的那种处理,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觉得处理得不合适。但这些对于演员来说其实不那么重要。 除了那段戏以外,和范伟在厕所中的第一次对手戏,我也不太满意。主要是看了他太多的喜剧,一看他就想笑。 “桦林舞王”就睡了一个小时 跳舞,是马德胜案件之外的一个生活状态,也是他20年变化后,第一次亮相。在我看来,那是他与案件断崖式的一次诀别。 怎么展现一个老头的生活?遛狗、逛菜市场、下象棋,我们都想过,但是后来导演觉得都没有跳舞好,跳舞有劲。 我之前做戏剧,是有很多身体上的训练的,但是舞蹈这方面我确实没有太多经验,于是我找到了一个舞蹈学院的老师。 我发现国标舞特别有魅力,大量旋转是肢体的拧转,是上身与下身的拧转。肚脐眼以上为上身,肚脐眼以下为下身,上身与下身进行相反方向的拧动,就是他们说的拧毛巾。 身体在不停做着对抗,又和舞伴有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浓墨重彩的情感交融,这东西确实上瘾,展现马德胜也特别合适。 桦林舞王马德胜图/受访者提供 和老师学习之后,又在昆明当地找到了一个舞伴,这个舞伴可以算是半专业的,她跟我说短时间内我不可能学会这个舞。 后来我也释然了,我就把跳舞当作一个表演,去寻找舞蹈中的感觉,马德胜跳舞要展现的核心也不是专业性。 跳舞的那场戏是一个早上拍摄的,前一天拍戏拍到了凌晨1点,我回房间躺了一个小时就又被拽起来,咔嚓就又给脸上贴了一层皮,又化了5个小时。 其实状态非常不好,我曾经和导演说,能不能让我休息好了再拍,哪怕睡3个小时也行,但最后时间档期都不合适,就拍了。 跳起来以后我窥探到了马德胜的生活,那个心里不愿意和别人展示的那一面,那个一直跨不过去的坎。 看上去马德胜老了,也变了,但是又有好多东西没变。最后他没有被选上参加比赛,这给了他人物性格的一贯性,也让他最后加入三人追凶组,提供了可能性。 戏剧和影视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戏剧没有办法看监视器,没有办法重来,每一场演出演完就完了,第二天再演也是不一样的。 影视剧的优势就在于,导演可以看到监视器,这一条不行还可以再来一条,我此前是不习惯看监视器的,我不喜欢审视自己。 观众的评价我也很少看,演员只是一个助推器,把角色带到观众面前,任务就完成了,我就要从主体中开始脱落,或许马德胜在播出后,生命还在继续生长,每个观众都会赋予这个角色不同的感受和意义。但是对于我来说,马德胜已经结束了,后续的这些都跟我没关系。 真正舒服的感觉是坐着,但不说话 小时候我没想过当演员,就是老师说我声音挺好听的,我就稀里糊涂考了中戏,也就是因为上了中戏,所以我一直在做戏剧,当年如果考了电影学院,没准我一直都在拍电影。没想过为什么,就是觉得应该做。 生活是个很危险的东西,表演多多少少可以躲避一些危险。做戏不能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危险,但是可以过渡一下情绪,前提是你要相信戏剧和表演的能量。 我在北京西边的香山脚下,租了个房子,每次结束工作我开车返回那里,都会经过一条长达一公里的梧桐树阴,我把那个地方叫做“树洞”。 多少烦心事,钻进“树洞”回头看城市的时候,就都没了。我会把车窗摇下,呼吸空气中植物的味道,那种感觉对我很重要。 但有一天,我回家时发现,为了修一条轨道交通,道路两旁的梧桐树都被砍掉了,我顿时感觉自己家的大门被拆了。 那个晚上,我开着车号啕大哭,一边哭一边骂,但我也不知道骂的是谁。 演员也是人,也会有各种情绪,当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创作关联上,那在我看来都是有好处的。在我看来想要做一个好演员,首先要做到时时刻刻关照自己内心的状态,自己到底是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毕竟最后是要用身体去创作的。 我知道你们特别想听我那种故事,此前一直苦哈哈地演话剧,日子过得贼惨,吃糠咽菜,后来终于把握住了一个什么机会演了什么戏,让大家认识了我,从而喜欢上了我。 但这不是我的故事,我也编不出来。的确,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和认知也发生了改变,我现在也没离开戏剧舞台,反而觉得影视剧积累下的东西,尤其是那种细腻的控制,对于自己的表演是有价值的。 陈明昊饰马德胜图/受访者提供 此前我总认为要保持对创作真诚的态度,但是这些年我觉得还需要再勇敢一点,勇于去突破一些什么,《漫长的季节》给我的感觉就是,和一群真诚的人,勇敢地做了一件事。至于说这个事你们看到是好是坏,是在网上打了5分还是1分,那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 我现在很舒服地待着,你来打扰我,问我这一大堆问题,我挺难受的,我其实想骂人。但是我控制住了。 我记得有一年在乌镇,演完戏已经半夜了,大家都没散,还在那聊着喝着,我就拿着一瓶酒找了个沙发窝在那,一会过来个人和我说两句话,喝两杯酒。大部分时间就我自己那么待着。 我应该是挺累的,但是没睡着,现在回忆一下那感觉很舒服。 “坐着,不说话是最舒服的。” 记者:胡克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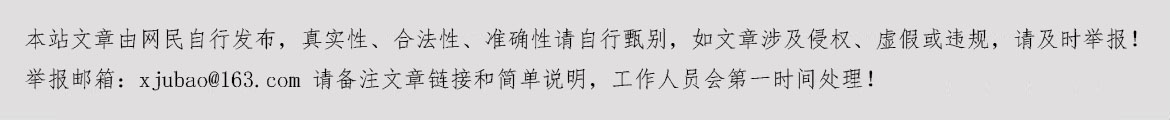
|
 鲜花 |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 新闻资讯
• 活动频道
更多




